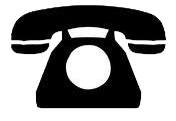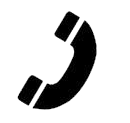纪王崮:王的长城
1
那些远离道路的小山,静静地投下深深浅浅的影子。大地是一面镜子,广袤而明亮。连一只蚂蚁的路线都清晰可循,更不要说这些雄踞的大地之子。一座座大小不一的高山城堡次第涌现,远看,仿若戴着平顶的帽子。当地人叫它们“崮”。
崮是大地上的塑像,巧夺天工,与被庄稼围拢的淳朴的村庄唇齿相依。民间的智慧,针对具有家族特征的崮群相继命名,孟良崮、东汉崮、锥子崮、云头崮、马头崮、莲花崮、歪头崮……那是智者由眉目间些微的差距,参与天地事物的明辨。崮,生了根须,静静地生长,单单属于沂蒙腹地的标识被指认,难以模仿。崮,这有着乡音缠绕的肖像的字形,也会根植某个少年的名字里,呼出的声息,恳切而绵长,奔向丰饶的大地深处。
民间,是一个平和安静的词语,也是深不可测、包罗万象的所在。历史上的每一桩事件都会在其中生发,隐没,究竟是销声匿迹还是暗藏玄机?在民间,空气中流淌着的传说,与淙淙的山泉一样清凉,与黑夜的面目一样神秘。民间传说沿着遗落的线索,以代代相传的方式还原真相,历史的轨迹呈现意想不到的曲折。没人在意讲述者是否添枝加叶,想象力似窖藏的陈年老酒,那气息令人沉醉。
泉庄人把境内最大的崮叫做“纪王崮”,源于传说,日渐为史引证。清康熙十一年《沂水县志》中记载:“纪王崮,巅平阔,可容万人,相传纪侯去国据此。”末代纪王的去处成了历史的谜。秘密被时光封存,随风而散的零星碎片,成了需要拼贴才能建构的缄默的物证。再也寻不到一个如此壮阔的崮顶。山巅上腾起的炊烟一下子就卷到了云里。那么,住在崮上的人似神仙了。没人说得清从什么时候开始,祖先在此繁衍生息。古村落的遗址犹在,而今的“崮上人家”延续着纪王崮数千年来不绝人烟的传奇。传说不是空穴来风,一些陆续出现的物证试图还原丢失的真相。农人耕地时发现了铜、板瓦残片,甚至遗落的簪子。疑问开始推向更远的从前,想象遥远的原住民,想象崮顶上依稀残存的真的是传说中纪国古城的遗址?
2
纪国乃东夷古国,姜姓,始建于商朝后期,周灭商后,接受周朝封侯。故城在山东寿光县城南十四公里纪台乡纪台村。纪国疆域广大,起兴于东海赣榆,后扩张至寿光建国,盛于齐鲁。诸侯争霸,纪国或兵戈相见,或参与会盟。《春秋左传集解》载:“鲁隐公元年八月,纪人伐夷。”即公元前722年,纪国兴兵伐夷国。纪国也曾攻打过齐国。纪侯姜季率部,占领过距齐都五公里处,迫使齐胡公徙都薄姑。莒国与鲁国不睦,经常发生边界摩擦,“鲁莒争郓久矣”。纪国出面调停。《左传》隐公二年载:“冬,纪子帛、莒子盟于密(今沂水),鲁故也。”在纪侯的斡旋下,公元前715年,鲁隐公与莒子会盟于浮来山银杏树下。自此,鲁、莒、纪结盟,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。联姻亦是纪国的外交谋略。公元前721年10月,纪侯娶鲁惠公女儿伯姬为妻。五年后,伯姬之妹叔姬再嫁与纪侯。纪侯则嫁女与周桓王为后,融和与周王朝的关系,藉周王威慑日益强大的齐国。
齐国与纪国同宗,两国封地比邻,纪国故城与齐都临淄,近在咫尺。历史不曾遗落任何一桩大事记。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载:“哀公时,纪侯谮于周,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,是为胡公。”从此,两国结世仇,“齐欲灭纪”。几经鲁桓公调停,甚至于公元前695年,促使齐侯与纪侯会盟于黄地。而齐灭纪的决心已定。未几,鲁桓公被急欲称霸的齐襄公谋害,纪国顿失后援。两年后,齐率部赶走纪国郱、鄑、郚三邑百姓,占领其地。至公元前691年秋,纪侯之弟纪季以一邑之地酅入齐成了附庸,以存宗祀。纪国势穷力蹙,纪侯向鲁国求救。鲁庄公疾往郑国滑地与郑君子婴商议救援未果。时间降至公元前690年夏,齐举兵伐纪。《春秋》载录纪国本事,庄四年成了重要的纪年,“庄四年,纪伯姬卒;庄四年,纪侯大去其国;庄四年,六月乙丑,齐侯葬纪伯姬”。
大去其国的纪侯何等悲怆,离开故国,一去不复返。直至“庄十二年,春王正月,纪叔姬归于酅”。归来的纪叔姬,带回的只有一个消息。历史曾无比真切地一次次现身,终被时光追逐成了行囊中似真似幻的影迹。而今能够连缀起来的只是一些冷静的事件,简洁得仅剩下了想象。即使亲眼所见都会生出差池,更何况这些远距离的纸端的辨认。消逝远比洪水迅疾,一切归于沉寂。在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上,由于缺乏逼真的场景而难以引人入胜。得寻到一处现实的土壤,才能唤醒所有逝去事物的记忆。从清晨出发,去寻找黑夜。循着隐没的事物的落点,探秘者听从大地秘密的召唤。不知所踪的纪侯究竟去了哪里,那为史书略过的八年,驻足何处?清道光七年,《沂水县志·舆地》试探着托出历史迷踪:“纪王崮相传纪子大去其国居此,故名”。相传是揣度,也是因为相承的久远。所有的视线再次落到矗立在大地深处的高山城堡。想当年,于苍茫中孤军独行的纪侯望见的是什么?逝去的疑惑开始慢慢地在现实面前消解,一切都由来已久。那被命名为纪王崮的山,据说泉庄乡深门峪村的一个自然村,也叫纪王崮。
3
五月的午后,一望无际的原野倾吐灼热的气息,把心底的热忱毫无保留地敞露。白生生的光线直直地倾泻在头顶,与登山的路径一致。倏忽间,坐在车里的人已然忘记了贴着山体的盘旋,而以为是直直地升了起来。人仿佛真的是在半空悬浮,白光耀眼,望着一侧的沟谷、乱石,不由得心生怯意。待沿陡直的青石阶一路登攀至顶,方才安顿。站在海拔577.2米的纪王崮,发现果然“巅平阔”,近四平方公里的面积,南北绵长,岂止容万人。
平顶,四周陡崖。这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堡。站在崮顶才发觉大风在头顶上飞。它不是从哪道山门闯进来的,它是天生的,这里是它的地盘。所以,大风会冷不防从树丛中钻出来,从石缝里探出头,抑或从天空俯冲,像一只大鸟,一只凌厉的鹰。当远处的天空真的出现了鹰的踪迹,敬畏之人在大风中行注目礼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,自打从前的西大崮变成了纪王崮,崮上就不单单长树,还生出多得让人数不清的传说。天长日久,传说变成了树,变成了泉,依旧鲜活。那株枫杨树,又称平柳树,从巨石的臂弯兀自长出,历经千年,早已石树一体、石树一色,当地人将此石抱树奉为神树。最有名的泉有两眼,一处叫走马泉,一处叫胭粉泉。泉水甘冽、清澈,供给驮运粮草的马匹,也充当美人梳妆的六角明镜。伯姬和叔姬在民间被唤作胭茹和姒粉,这两位美丽娇柔的女子,在泉水的映照下愈加明艳动人。
城堡自然有城门,叫做朝阳门,水西门,凳子门,坷垃门,塔子门,走马门。六个城门中,当属水西门最是险峻,飞鸟难行,所以又称雁愁门。走马门的地势最为平缓,马儿可通行。途经的泉,就是走马泉。并排六个饮马槽,六匹骏马泉边饮水可谓壮观。经由走马门,通向的是山下一个叫深门峪的村庄。古城墙犹在。那些立于崮顶的巨石是突出的,仿佛坚不可摧的壁垒,无论颜色抑或质地,均与旁处的石头和岩层迥异。巨石切割的石块,千钧之重,历经数千年而岿然不动。古城墙如何建造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谜。究竟是在冬季泼水成冰,经由滑道,用绳子将巨石打捞上山,还是利用木块做滑轮,由“木牛流马”牵引至顶。到哪儿叩问绝顶智慧的古人?可以寻到的纪元台也是由巨石垒成。这个当年纪王祭祀的平台,刻有东夷部落鸟夷的图腾,玄鸟,即四灵之一的朱雀。纪元台最主要的精华是伏羲氏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的八卦。纪王在此祭天地、祭祖先、祭社稷,企盼以虔诚感天动地。盟誓的呐喊该也由此集聚,在崮顶回响。于是,西大崮成了纪王崮,拥有了王城的规模。在齐鲁的边界,在幽谧静寂的群山包围之中,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国的秘密。它不会被风化,因为有崮忠实的守候。那六道天然的城门,唯留下鲜有人至的深门峪。深门峪低沉不语,守口如瓶。
4
纪王宫是纪王崮唯一的建筑,在遗址上复建的纪念碑。甚至没有高过一棵大树,质朴的外观很容易被发现,有些孤单,但并不觉得突兀。这座在原址重现的行宫,谨慎地按照西周的宫殿建筑式样。重檐庑殿顶式建筑的纪王殿,面阔7间,广32.4米,深16.06米。周围环绕28根廊柱,建筑面积512平方米。观者揣度,这不见得是原貌。至于最初是什么样子,谁也没见过。而遗址具备天生的吸引力,于是,还原成了一桩势在必行的行动。
一楼是具象的,具体到固定的生活场景。它们如此简洁,没有一丝多余的陈设。被展开的日常生活慢条斯理地隔断了遥远的时空,只呈现凝固的瞬间。当翻阅被公布的王宫生活,人群中有人开始对照个人的现实生活。没有谁怀疑其中饱含的想象力,而想象力的延伸正由着另一种途径——一张张深入其中的影像继续。通往二楼的木质楼梯是狭窄的,听得见不安的足音。还好,行进间有跃动的光线细心地牵引。二楼是一处展馆,塞满了漫长的历史,长得让人记不起从哪儿开始。当时间止步,当现实变成历史,变成了安静的文字,回顾与沉陷属同一种姿势。来者立在一处礁石上,四周是涌动的黑色的海浪,声声不息。历史浮现,栩栩如生,在叙述者缜密的探究下,完整得像一块独立的天空。盘踞在展馆中央的纪王崮沙盘复原模型,以崮独特的挺立,宣言般地证实着王城的存在。没有人再怀疑传说。当新闻成了旧事,传说充当了预言。人们发现真相正沿着传说的路线游走。民间是乔装的知情者。民间传说不再是好看的花边,而是有着细致的可以探究的纹理。瞧,事实多么郑重地正沿着花边奔跑。那场波及全国的重大发现为人瞩目,原本寻常的施工现场化身千古探秘之旅。那实在是一场轩然大波,至今尚未完全退却。独自站在空荡荡的静寂的现场,周匝烘托大幅夺目的图片和文字,一同守护着以往的沸腾。在这个临时搭建的架子下,被标示的位置,整齐的坑道,千年的尘土,遗留的马骨,严守秩序一样严守尘封的秘密。两千六百多年已经足够得长。历史是未知的,过去包含巨大的秘密——那些全然未预料的事情。相较于未来,旧事物总是更让人感觉新奇和惊讶。历史的天空一部分被隐没,隐于地下。喧哗散尽,以消逝还大地以寂静。对于猝不及防闯入的另一个世界,久远的过去保持青铜器般的沉默,即使被哔哔啵啵的光线照耀。时光锋利,削铁如泥。
下午的光线重了,开始由王的城自上而下地慢慢滑落。滑过两军对垒的疆场,滑过奇异的地下冰宫,滑过险峻的崖壁栈道,滑过幽思的望乡台。温凉河安静,马连河安静,虎头泉、马蹄泉和响泉闻见了什么消息,开始窃窃私语。那天,无论走到哪儿都被大风奇袭,临行前只好用手遮住飞舞的头发,露出面孔,一并留住落至原野上的绵延的崮群。大风一路追随,是想赶往山下喝桃花酒吗?
(也果)